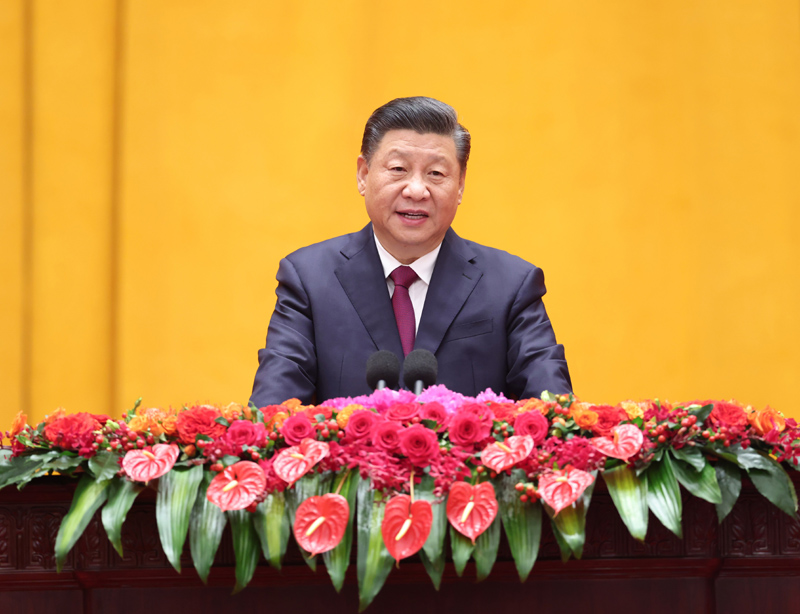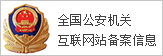於可训简介:1947年3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一、“好的文学批评要有个性和温度”
王海龙:於先生,您好!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晚辈来为您作专访。您是武汉大学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自您1977年考入武大中文系并留校至今已44个年头了,可以说是新时期武大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了。记得您刚留校时,是在文艺学教研室,后来才到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您觉得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治学有什么影响吗?
於可训:有很大影响。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史研究文学的发展变化,文学批评研究文学的当下状态,也有人说是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韦勒克、沃伦)。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位学者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在谈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时说,“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
对我个人而言,有了文学理论的基本训练,在从事具体作家作品批评的时候,能迅速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作理论的归纳和提升,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概括力和阐释评价的理论深度。对我从事文学史和其他方面的文学研究,好处就更多了,因为任何文学研究,都要有对材料的鉴别提炼能力,对经验的抽象概括能力,这些都少不了文学理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文学理论提供的一些观念和方法,也是文学史和其他方面的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学理论的指导和引导,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就缺少了“文学的”依据,反过来,也不可能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经验变成积极的理论成果。我留校后从事过六年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自觉受益匪浅。
我从文艺学转到当代文学,除了工作的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更新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出现了一批当年被称为“崛起的一代”的青年批评家,我忝列其中,是这个群体中年纪较大的成员。因为那几年我在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之余,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写作,写的评论文章较多,也小有影响,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陈美兰老师,也是资深的女评论家,就把我要到当代文学教研室来了。所以,我的转行,还留有一个时期文学批评发展的印记。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混迹于一代人中间》,就是记载这段经历的。
王海龙:是的,理论与批评是有机互补的。记得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功能,能请您进一步谈谈一个好的文学批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吗?或者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
於可训:我理解你所说的“好的文学批评”,是指那些合乎文学批评规律的文学批评,或者是优秀的杰出的文学批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好的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有对批评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感悟能力。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要把文学作品真正当作“文学的”作品来读,不能当作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或其他学科的文本来读,更不能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产品来读。只有这样,批评家才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各学科的案例和证明、或追求官能的刺激和满足上面,而是专注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在这个基础上理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领悟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意味,有了这样的感性经验或曰审美感受,才能进一步对文学作品的意义作出阐释,对文学作品的价值作出评价。
其次,在进一步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评价过程中,就应该有对阅读文学作品所获得的感性经验或审美感受加以提升,使之上升到一种普遍性高度的能力。批评家从阅读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感性经验或审美感受,是个体的、自足的,文学批评却要通过一种理性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满足社会人群的需要。别林斯基说,批评的任务,是 “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通过这样一个理性提升的过程,文学作品具体个别的艺术描写,才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否则,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只是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作品中主人公的遭遇,也只能博人同情,都不可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代的一些“红色经典”,如《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和《红岩》等,也只是一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却不可能让人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更不可能激励今人的革命精神和斗志。文学批评固然要避免“过度诠释”和不当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好的文学批评”,却需要这种必不可少的理性提升和恰如其分的阐释与评价。
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评价,都需要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以及一般社会知识的参照,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批评家主观认定的结果,而是在参互比较中显示出来的,要依靠一定的理论方法才能得到说明。只有建立一个多学科全方位的参照系统,才能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得到有效的阐释和评价。这就需要批评家具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这也是对一个“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文学批评的要求。“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文学批评,要像别林斯基说的那样,善于“在个别的现象里去探寻并显示该现象所据以出现的一般精神法则,并且要确定个别现象和它的理想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这个标准不一定每个批评家都能达到,但“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文学批评却应该怀有这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
王海龙:听完您刚才关于好的文学批评标准的阐释,让我获益匪浅。也正是您的这份理论洞见,让您的批评实践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生命体证的温度。如您的《王蒙传论》,虽然是个案研究,却非常有深度有温度有个性。然而反观当下的文学批评,却频繁出现“失语”和“缺席”的现象,理论与批评往往脱节甚至各行其是,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於可训:从道理上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不会脱节也不应该脱节的,这个道理在上面提到的两位美国学者的书中都有相应的说明,我已引用过他们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没有文学理论提供的“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就不可能进行。通俗地说,文学批评是借助文学理论的话语说话的,没有文学理论提供的话语资源,文学批评就不能发声。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理论与批评脱节,而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脱节。很长时间以来,一些批评家往往热衷于跨学科引进一些理论概念或思想命题,然后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求证明,把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或细节,甚至整个文学作品,都当作这些跨学科的概念和命题的案例,相应的“文学”理论反而无用武之地,结果便导致了文学理论的“失语”和“缺席”。这样的批评不过是假文学批评之名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因而在文学理论“失语”和“缺席”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失语”和“缺席”。
很长时间以来,文学批评存在着一种刻意标榜宏观视野和滥用跨学科知识的倾向,我曾经批评过一种不读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家和不读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认为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只要祭起“无边的视野”和“跨界的议论”这两样法宝,就不愁作家作品不入其彀中。这是造成当下文学批评“失语”和“缺席”的主要原因。
至于我的《王蒙传论》,不敢说有什么深度,我只想老老实实地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用的不过是古老的“知人论世”的方法,今天也叫社会历史批评,或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选择以王蒙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在当代社会颇有代表性;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代表性,较之其他当代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几乎贯穿了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学的全部历史,经历了其中的跌宕起伏、曲折变化。以这样的作家作个案研究,既可以透视当代文学的历史,又可以透视当代社会的历史,我用王蒙的人生和王蒙的创作互证,跟一般作家评传的写法稍有区别,所以叫做“传论”。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去理解和阐释王蒙的人生和创作,融进了较多的个人感受,所以显得较有个性和“温度”。
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首先是一个方向性的命题”
王海龙:您刚才分析的当下文学批评的“失语”和“缺席”的原因非常在理。纵观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一直强调文艺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您能具体谈谈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吗?
於可训: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作过很多精辟的论述。我能谈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和体会。
从源头上说,文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理应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原始的文艺创作都包含有自娱自乐的成分。后来,由于社会分工,尤其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文艺创作慢慢地就成了文化人的专利,成了主要由文化人完成的一项精神创造活动。由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些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化人,隶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创作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和少数拥有文化知识的人服务的,为他们所欣赏和接受。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既没有欣赏和接受文艺的条件,也没有时间的余裕,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文艺的服务对象之外。
近现代社会,普通民众和劳动人民逐渐成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人民群众从作为“改良”的对象,到作为“启蒙”的对象,到成为革命的主力,改变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向。近现代文艺从为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服务,到倡导普罗文艺,追求文艺的大众化,为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众觉悟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工农兵方向”,文艺逐渐成为人民群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在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则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艺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文艺只有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结合起来,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服务,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应有的作用。
这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文艺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本来也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问题是,在创作实践中,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个人置放于人民之外,因为强调个体经验和艺术独创,而排斥人民群众历史创造的经验,与人民群众对艺术接受和艺术鉴赏的诉求对立起来,结果不免脱离群众,变成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这样的文艺创作也就谈不上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艺扎根人民,文艺家深入生活,永远不会改变。因为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而是一个方向性的命题。深入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时是为了解决作家转变立场、熟悉群众等问题。虽然由于当今社会资讯发达,人们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和熟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上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也显著提高,作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明显拉近;同时由于现代生活的同质化,作家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日益接近,使得转变立场、熟悉群众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就过时了。
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与生活的天然联系和血肉关系,同时也在于它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如果不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些变化,只满足于随着社会潮流滚滚向前,就事论事地反映这个过程,充其量只能得其表象,而不能深入揭示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本质内涵。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而是新时代如何扎根人民、深入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与中国古典文学所处的农耕时代不同。信息时代资讯发达,在给作家了解社会、熟悉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造成了很大影响,以致于有些作家只满足于依靠各种媒体和自媒体、尤其是网络信息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种依靠媒体信息写作的“资讯写作”现象。这些新现象、新问题无不凸显着置身于全球工业化、信息化浪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各种现代资讯,在充分利用现代资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摆脱对它的依赖,是今天的作家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海龙:文艺为人民既是一种创作理念,也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很多人都反感在艺术创作中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干预,甚至希望为艺术而艺术,不要政治,不要意识形态。关于文艺创作或者批评与政治的关系,您怎么看呢?
於可训:不管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不可能离开政治,都会受政治的影响。这是因为,文艺和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问题。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的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是有层次的,并不都处在一个平面上,政治、法律、道德等,是离经济基础较近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艺术等,则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的关系,有人就误以为文艺高于政治,可以不受政治影响,去追求脱离政治的纯艺术,这不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也见不到完全脱离政治、不受政治影响的艺术。
问题不在于文艺要不要政治,愿不愿意接受政治的影响,而在于如何通过政治,去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集中表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要求,往往集中诉之于一定的政治,通过一定的政治集中表现出来。文艺通过政治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在政治的正确引导下,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趋势,才能正确地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批评同样也有一个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问题,也需要政治的正确引导。
王海龙:您说的没有脱离政治的文艺,我很赞同。文艺创作和批评不能远离现实,更不能张冠李戴,作为中国当代的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国情,积极回应中国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对此怎么看呢?
於可训: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近年来也在文章中谈到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流脉,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一定要通过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以一种新的阐释和理解,诉之于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前人的文化创造,是根据彼时彼地的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前人留下的历史文化材料和思想资料,凝聚了前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是留给今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这些文化材料和思想资料,必须根据今天的情况、根据今人的理解加以阐释,在这个过程中,让今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前人达成默契,相互融通,彼此照亮,结出新的精神文化成果。这样,才能对今天的社会发生作用,也才能代有传承地流传下去。
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受西方影响太深,言必称希腊,例必举欧美,连名词概念也大多取用西方,对自己的传统反而比较陌生,对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和民族特性、中国文化典籍的状况和源流等问题,都缺乏必要的了解,或者只满足于一些基本常识,浅尝辄止,不愿意深入堂奥、探索幽微。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必要提倡多读一点中国的书,让大家更多更深入系统地了解一点中国文化知识,这样,才能谈得上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连自己的传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或没搞准确,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没了对象和前提。这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我们大家都要朝这方面努力。
三、“用材料和事实说话”
王海龙:2018年,十卷本的《於可训文集》正式出版,这套文集可以视作您对过往治学生涯的一次回望和总结。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您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也是书写者,更是批评者、研究者。那么,继承传统与回应当下,二者应该作何解呢?传统的过于遥远,当代的过于新近,尤其是对当代文学来说,它永远是进行中的,对它的批评也必须是“在场”的批评。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隔与裹的问题呢?
於可训:现在大家都在谈继承传统,我们在前面也谈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但对什么是传统,我们却没有深入细究,因而在谈论中常常出现歧义。在许多人看来,传统似乎是一个陈旧的器物,放在一个老房子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继承传统也就是从这个老房子里把某件器物拿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继续使用。这种理解显然是把继承传统等同于继承家产,是一种静止不变的传统观和机械实用的传统继承观。其实,传统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而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精神联系。对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要进入和把握这种精神联系,并把这种精神联系延续下去。延续这种精神联系的方法和路径,就是根据今天的现实诉求,根据今人的理解,对过去年代的精神遗产作出新的阐释。这种新的阐释,连同过去年代的精神遗产,又被后一世代的人们所接受、理解和阐释,如此递嬗,就形成一种代有传承的道统或文统,这就是所谓传统。所以,传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传统不仅是昨天的历史,也植根于今天的现实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的“继承传统”与“回应当下”,二者之间不但不存在矛盾,而且还存在着一种相互观照、相互发明的关系。传统给当下提供理解和阐释的对象,当下对传统灌注新的精神元素,激活传统、赋予传统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样二者就不是相隔遥远、背道而驰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也是如此。虽然当代文学批评永远是“在场”的批评,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就是“缺席”的。恰恰相反,不但我们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一套概念、命题,“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都来自传统,都是从前人的经验和理论中生发出来的,都是某种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传统孕育的结果;而且我们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进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传统存在着紧密的文化关联,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的价值体现。即使是社会政治的标准,也关联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不能割断传统的。
王海龙:您说得非常好。但是亲近传统不能流于附庸风雅,您之前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而如何避免消费传统,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识见。在文学艺术领域,那就是对中国文学史要有很好的把握。您既是文学评论家,也是文学史家,先后出版了《新诗体艺术论》(1995)、《中国当代文学概论》(1998)、《当代诗学》(2000)、《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2005)、《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2006,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当代卷》(2006,主编)等文学史著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将编年史引入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您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种致思路径吗?
於可训:把编年史的体例引入文学史的编写,不是我们的发明,古代文学史编写前已有之。我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不过是较早地把编年史的体例用之于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很长时间以来,基本上是沿用类似于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即以作家为中心,分章节论述其生平和创作,只不过比纪传体的史书多了一个社会文化背景的交代和文学发展状况的概述。这样的体例有一个好处是,便于集中讨论作家作品,能较为完整地窥见一个作家的创作全貌;缺点是,把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集中起来讨论,很难把握产生这些作品的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发展状况,因而也就难以从单个作家的创作中去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也难以对作家作品作出准确的历史判断。
编年史体例因为是着眼于“史”,而不是着眼于“传”,因而历史的线索鲜明突出,且因为是依年系月、依月系日,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文事,包括作家作品的发表、出版,作家的生平行状、文学活动和文学会议,对外文学交往等等,比较接近历史的原貌,能较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情境,为从历史现场的角度阐释和评价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背景和历史参照。
这种编年体的文学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改变了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一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偏向,让文学史真正通过材料和事实说话,而不是由编写者先在的理念主宰。长期以来,文学史编写者往往先有一个外在的或预设的述史观念和评价结论,而后再根据这种观念和结论去圈定、选择相应的文学材料入史,结果就不是从材料和事实中得出文学史的结论,而是由编写者的观念决定文学史的判断,文学史料只不过是编写者预设观念的一个证明。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一种观念的循环,而不能真实客观地展示文学史的历史面貌,也不能对文学史实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编年体的文学史用材料和事实本身显示作家作品、创作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活动的意义价值,论从史出,是一种“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我曾经谈到用编年史的体例编写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方面是想尝试一下被现当代文学史家所忽视的编年史的编撰体例,也想借此机会使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的体例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得到复活和应用,以此对长期以来已逐渐趋于定型的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体例来一个较大的突破。
第二个方面是想借助编年史的体例,重新搜集、发掘、整理为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所遗漏或舍弃的重要史料和史实,以便为构造新的更完备的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个更加系统全面、扎实可信的研究基础。同时也想借助材料和事实的力量,改变文学史的某些定论和成见。
第三个方面是想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促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和变化。近25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迭经变化,成效显著,但近些年来,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模式,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本项目的研究在突破这些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希望进而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新的革新与变化。
第四个方面是鉴于当今学界受时潮影响,学风日趋空疏和浮躁,针对这种情况,希望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培植和倡导一种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学风。这种学风一方面源于中国深厚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与近代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相合,在文学史学科中尤其值得重视。
这种编年体的现当代文学史,包括分体的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现在逐渐多了起来。这种文学史的出现,给文学史编写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也是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历史著述体例的一个积极的成果。
王海龙:您在武大工作四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作为一位创作和批评兼善的大家,您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可以给年轻人分享一下吗?
於可训:我是从事文学教育的,只能说一点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我觉得一个文学系的学生,首先要尽可能多地阅读文学作品,这是第一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经验或曰审美感受的基础上的,没有这种感性经验或审美感受,说什么都是空的。读的作品越多,获得的感性经验或审美感受越丰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才有话可说,才能说到点子上,否则,就只能靠一些空洞的理论和似是而非的跨学科知识说话。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理论和多学科知识,但与从阅读文学作品中获取感性经验或审美感受相比,有主次之分、主从之别。现在的文学批评往往不读作品,或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一目十行地读作品,文学研究也往往是借助转述文学作品的二手资料,并不认真地去读原作,结果所作的判断和分析都不能落到实处,对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也就发生不了实际的作用。这种文风和学风亟待改正,希望就寄托在青年学生和年轻的学者身上。
王海龙:如果让您展望一下未来,您下一步有什么新的规划吗?或者有什么旧的规划亟待去实现的?
於可训:我在学校荣休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我要像前人一样,来一个衰年变法,由一个学者,变身为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所以退休后的这几年,我开始接续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作品,2021年结集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叫《乡野传奇集》。我同时还在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给他们上课,指导他们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也写一些理论文章。我没有什么未来规划,只想在力所能及地干好我的这些已非“本职”工作的同时,专注于我热爱的小说创作,在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工作之后,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一下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看看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我的一个老师说,我们这些教文学的人,自己不会炒鸡蛋,却要教人家鸡蛋怎么炒。我这回就想自己学会炒鸡蛋。
访后跋语
由于疫情防控的因素,我和於师可训先生是在线上进行的书面访谈。先生虽然贵为武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但在访谈交流中丝毫没有架子,访谈的回答亲力亲为,这令我尤为感动。而且,先生对待访谈非常严谨,还专门为一个表达较为模糊的问题跟我沟通,力求细致精确,让人无比感佩。在先生看来,没有脱离政治的文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而只有兼顾了文学理论的高度、文学史的广度、文学感知的锐度,才能成就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批评。大哉言,信可乐也。先生的博识雅正,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力量和未来发展,心生无限期待。
编辑:国龙

 甘肃春晚
甘肃春晚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