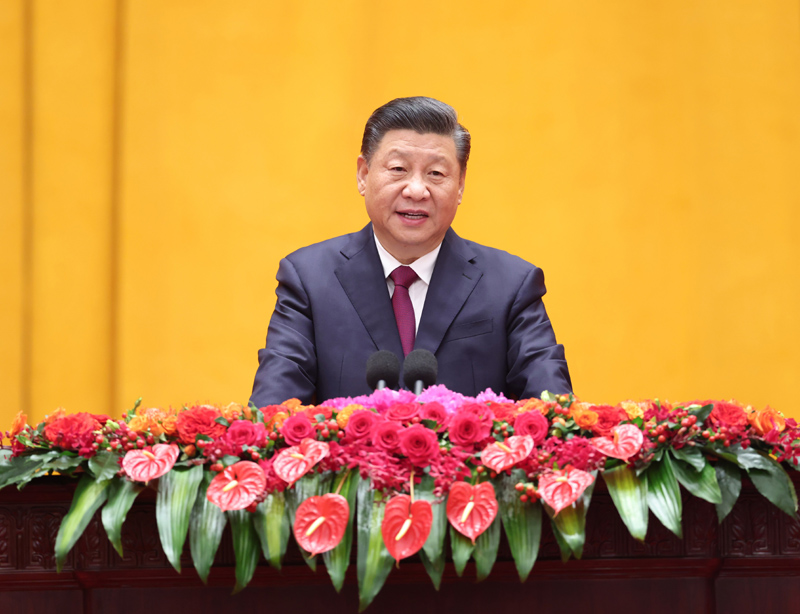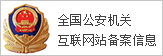我出生在河西走廊,古人笔下连春风都不能企及的地方。小时候对家乡的认识很具象,那是瑟缩在祁连山脚下盼望残冬快点过去的身影,在漫天风沙的浑黄中不辨东西的吼喊,父辈佝偻着的腰背永远那么的绝望凄慌,干瘪的肚子叫嚣着一曲曲空城计此起彼伏,村头枯树上的老鸹窝神秘而庄严地诉说着大槐树下的故事……一切都被定格在记忆深处成为一帧泛黄的黑白照片。
古诗里属于河西走廊的颜色是浑黄沉郁的,仿佛永远只有黄沙百战、大漠孤烟,梦里都充斥着铁马冰河、金戈烽烟的苍凉气息。不管是小桥流水、烟雨软柳,抑或远山苍黛、亭阁鸟鸣,青绿山水的画面上河西走廊的缺席似乎理所当然,水墨勾勒的诗画也难以承载祁连山的一声长叹。这就是河西走廊,那个曾经驼铃无数川流东西的汉唐四郡,飘荡着华美丝绸之香与飞天乐舞交相辉映的商贸孔道。
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繁华落幕曲终人散,历史遗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褪色的一尊旧泥塑,时隔百余个世纪惨淡吟唱着物是人非,葡萄美酒的醇香与横笛马背的春光,成了小学课本里靠着想象去凭吊的久远过往。再美好的梦想与雄心壮志,都会在一场又一场漫天沙尘里剥脱侵蚀,然后被迫妥协心存戚戚,无情地将一个风华少年捶打成一具麻木干瘪的胡杨根雕。出走还是留守,一直都困扰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躬身田地间越久就越是心生不甘,而手掌上不断增厚的茧子又时刻逼人屈服。于是,在那些身体与灵魂割裂开来的深夜里,我总是在想命运到底是什么?脚下这方土地的尽头在哪里?而我生活在此的意义又是什么?后来,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家乡,去往梦想中的远方追寻答案,离开河西走廊一走就是半生。远方的远方是故乡,年轻时不理解的深奥,会随着岁月的磨砺渐渐开悟,仿佛不经意间生命中就多出了一个叫做“故乡”的执念。午夜梦回霜鬓渐染,突然就特别想回去,因为之于满城烟柳的皇都你只是一个客居者,哪怕有房有车有事业,心底深处那一抹隐藏的执念都在提醒你,家并不只是一幢房屋,乡音难改就是最好的牵绊。
走出半生,归来依旧。必须承认,当重新踏上河西走廊的那一刻,我的心空前安定宁静,正如父亲曾教我撒种时说过的那句话:走直了、踏稳了,你就是个好把式。拼搏了半辈子才发现,终究还是难逃一个把式的命运,不过是将铁锹犁铧换成了笔杆子而已。改变了的是生产工具,没变的依然是身份,我知道自己的内在还是那个农家子弟,喜欢泥土芬芳脚踏实地。近些年来,我在不断尝试去触摸探索,以期用文学的形式描摹河西走廊,还原过往的繁盛、体悟历史的深沉,慢慢就理解了真正的河西走廊。脚步丈量过的行程里,每一个刻度的厚重都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承接,而岁月的余香更需咀嚼很久很久才能体尝其中真味,河西走廊尘满面鬓如霜的沧桑外表下,是一颗历久弥香的种子,正在等待更多有志者来挖掘、培土、浇灌,守护她的发芽开花,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收获异香满怀的文化之硕果。
接受创作《张掖传》的任务,使我感到既欣喜又胆怯。怕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不足以刻画这座城市厚重之万一,但又急于要将自己满心满肺的话语诉诸笔端,期待更多走出去的人回来共同坚守家乡,也希望外面的目光聚焦这方山水令她夺目生辉。总之,是带着丝丝功利之心的。及至后来,正式开始创作,研究城市历史的过程中起初的浮躁竟荡然无存了。一座城市的沉稳告诉我们,你来或者不来,她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离开还是留下,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人与城市早已在轮回的宿命中许下死生契阔的誓言,她给予你思想,你也在装点着她的容装,彼此牵绊相互维系,一如河西走廊与“四郡”之间看似有别实为一体的亲密。
河西走廊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体现在称谓上,好多人物、故事、方言、风土民俗横贯走廊多个城市,城乡山野的角角落落里它们都是互通的,写张掖历史与文化就难免与左右邻居城市有所重叠。譬如祁连山的传说,西游记里的故事,还有那些在河西建功立业、开拓江山的文臣武将,宣扬佛法舍利长留河西的大德高僧,赶着驼队长途载运货物的行商,和沿着走廊东西串联的乐舞诗词等等……正如江南的苏杭之于河西走廊的甘凉,气息相同、韵味一致,两者形同孪生。因此,一个出生成长在凉州的人定居甘州,并没有半点客居他乡的疏淡,对这座蓝天厚土黑河之畔的城市的热爱与留恋之情完全不输当地任何人。
张掖,粗犷中折现着柔情,细腻里宣示着豪放,还有些桀骜不驯野性外露,城市性格因此而矛盾复杂,时而温柔多情,时而暴躁易怒,让人总是难以捉摸不好亲近。城市的性格就是人的性格,河西走廊上大多数男人、女人都具有类似的矛盾性情,这是来自血脉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汇聚了多民族融合的象征。河西走廊最值得称道的城市就是张掖了,这里在很早时期就被誉为“塞上江南”,固然气质硬朗风骨铮铮,其实最能包容万相,纳得下山川湖泊、沙漠戈壁,也受得住风沙遮望、冰雪长天。在这里,你可以不温柔但不能粗鲁蛮横,可以默默无闻但绝不赞成庸碌懒惰,因为祖先马背驰骋的基因里就没有遗传下来懦弱和惫懒。所以,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勤劳坚韧,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安贫若素总能开出昂扬奋发的向阳之花,持续建设着青山绿水的家园。
张掖的复杂多元包括民族构成,汉武帝攫取河西开启了张掖历史上的移民先河,中原文化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冲,不亚于弱水之于黑土地的冲积,沉淀下来的不仅仅只是耕地墩堡、百家诸姓,还有多元合璧的历史文化底蕴。上马杀敌、下马耕种,能够茹毛饮血也可以精烹细饪,张掖的饮食都带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张掖在某种角度论也属于移民城市,汉代到近当代,从未停止过接纳移民的脚步,她敞开怀抱广纳四海,以最大的兼容之心赋予这里的人们一种独特的语调,江浙话、山西话与土语杂糅融合,就变成了张掖话。他们习惯走路背手,把入厕称之为“解手”,延续着大槐树的传承;他们喜食牛羊肉,需要借助高热量的食物来增加肌体免疫力抵御风寒,继承着边兵随时准备上阵杀敌的勇武;他们性格耿直豪爽,反感弯弯绕绕尊崇实事求是,骨子里保留了草原民族的单纯质朴;他们善于经营,可以种地也可以行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始终丢不下驼铃声声的旧梦……一曲八声甘州传唱天下,骨头上烙印了张掖的标志,走到哪里都能舒展臂掖,顶天立地。
八千年历史看甘肃,甘肃历史看张掖。四坝文化佐证了河西历史,走下昆仑之巅的西王母在弱水河畔建立起强大部落,襄助炎黄成就华夏文明。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文明交流,张掖从来都是传输带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里程,匈奴一路悲歌退出张掖,胭脂如血成为他们梦魂萦绕的颜色。你方唱罢我登场,沮渠氏乱中摘冠面北称帝,于崖壁间营造佛国胜土,梵花荼蘼了临松薤谷。隋炀帝封禅焉支,这是仅次于开凿大运河的壮举,震慑西域万国、博览中华雄风,焉支山便具备了泰山的伟岸。甘州大曲与胡姬歌舞装点着盛唐宫廷夜宴,见证了玄宗和贵妃劳燕分飞,也带着回鹘冲上万众瞩目的中原历史舞台。西夏护国寺上演了数度传奇故事,事关一个王朝与另一个王朝皇室血统的延续,六百年岁月将他们酿成一瓯迷离的老酒。肃王怀揣抱负迎来甘州最高光时刻,一座省府城市在河西走廊熠熠闪光,与古都长安东西辉映。中华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民族之战,杨家将的后裔们用鲜血诠释着精忠报国的意义,狼烟熄灭八旗铁蹄终究踏碎山河如梦。高总兵的府里装不下杨总兵的理想,饮马桥也难以阻挡人头落地,红颜渐老英雄末路只是故事,百姓们关心的永远是乌江镇的稻米收成如何,祁连牧场里牛马又产下了几只幼崽。品一碗难得糊涂的张掖臊面,谈笑一番黑水国地下的金月亮和金太阳,佐餐小菜与饭后甜点就都有了。去一次西路军烈士陵园吧,在那里足够令你懂得幸福是什么,一座丰碑从此就会长在心坎上。掬一捧山丹河的水浇灌黑土地,那两个外国人长眠的地方也有一座碑,他们跨越重洋牵起国际主义的情感纽带,用生命培育黎明,开启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气象,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格局。洗尽铅华、脱去盛装,张掖依旧还是最初的样子,可婉约亦可豪放,在八声甘州里低吟浅唱,在长河落日中琵琶弦动。“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盛夏的夜晚仍需棉被加身的是她,春风光顾羞涩遮面的是她,子规一夜啼明朝杏花满枝头的是她;晚来天欲雪畅饮何须提的是她,围炉听卷弦弹春秋的是她,灯火阑珊中风雪夜归人的也是她。张掖气候多变昼夜温差极大,早上还是春光十里柔情江南,夜晚有可能就北风萧萧雪花飘飘,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她了。
百里不同天,十里不同音。张掖的方言也很有意思,发音永远高开低走,总要以第四声来做收尾,且几乎用不到第三个声调,直来直去非高即低,似乎想要以此来证明他们不会拐弯抹角一根筋通到底的爽直干脆。开门见山,抬眼望天,在张掖人的心目中,只有不愿意攀登的高峰,没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深渊,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再难都要办成,自己选择的人生跪着也会走完。而所有这些性格特点,我身上全都具备,所以选择回到家乡一定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来到张掖写《张掖传》,既是我的宿命,也是张掖的宿命。城市是有生命的,通过追溯她的前世今生就知道了人的来处与归处。
本次创作《张掖传》,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以及新星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创作原则,是为“史学精神文学表达。”因此,我要创作的不是一部史志,也无意越俎代庖去抢史学专家的风头,和史志工作者的饭碗,只是基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加以文学化的叙述与加工,并融进了自己的思考,以及一些浅薄的见解。希望当这本书与读者见面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历史是通俗化浅显易懂的,是能引起阅读兴趣的具有故事性的一本历史读物,可以让读者通过《张掖传》来重新认识一个面目可亲的城市,让城市拥有灵动不再只是冷冰冰名称,那我自认为本次创作就是成功的。自然,一座拥有八千年文明沉淀的城市,仅凭数十万字是远远不能描摹其深层次内涵的,本书中所展现的故事和梳理出来的历史脉络,只是对张掖细密如织的网状历史进行了一次素描般地临摹,撷取了她丰满骨肉中有棱有角的部分来进行还原,一些毛细血管般的细枝末节并未顾及,框架式的内容比较多,并没有追求面面俱到。《张掖传》是我创作中的新尝试,也是张掖以传记文学主角展现自身魅力的开端,这绝不是结束,也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尽完美处还有待更多写作者来查漏补缺,更希望后来者一代接一代续写下去。因为中华长存,张掖长在,生命长续,文学就必然长青。低调中盛放,张掖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的一份子,必将在新时代重放光芒,开出团结幸福、文明和谐的绚烂之花。
对于作家来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堪比孕育一个孩子,从珠胎暗结到呱呱坠地终于面世,整个过程中遍经酸甜苦辣心情总是复杂难以言表的;又恍如一朵花的盛放,从种子发芽到破土而出开枝散叶,枝头绽放的瞬间只有自己知道曾经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每当这种时候,作家内心其实是虚脱的,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亦有一种细胞被剥离而去的空虚。不管读者眼里如何看待,在于自己而言美丑都是宝贝,敝帚自珍者如我总是习惯性地爱惜珍视。
本次《张掖传》的创作,算是我作家生涯里最难产的一次体验。所谓难,一方面体现在文本创作上。为一个城市写传就需要了解她的前世今生,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坊间轶事的收集是个不小的工程,于浩繁烟海的城市过往中打捞遗珠珍帧,思想和精神在时光的缝隙里古今穿梭,筛选甄别、论证阐述,必须具备史学家的严谨和专业性,又不能失却文学的意趣与浪漫,是个很大的挑战。诚然,这些都是身为写作者的份内事,习惯于苦中作乐也没什么可赘言的。真正的艰难非为写作,而是来自写作以外的各种压力。《张掖传》初稿完成时,有所谓“专家”通过市文联发来意见,批判本书数据性东西缺乏罗列,不能有未经证实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不该带有个人见解和思想……种种意见不一而足,令人发笑之余心生无奈。此时才发现,在我们的文化群体中,相当一部分“领头人”居然还没有搞清楚《传》与《志》的区别就开始挑刺炮轰了。不得已,只好专门写了报告去阐明“传记文学”和“志书”到底是什么。这种多出来的工作既消耗精力,又让人无可奈何,颇感郁卒。
好在,所有的困难阻挠最终得以化解,这本书还是如期出版了,欣慰、欣喜,感激、感谢,需要鞠躬致意的人很多很多。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张掖市委市政府、张掖市委宣传部对本人和本书的大力支持与勉励,感谢文史专家、学者给予本书的肯定,感谢合作伙伴程琦先生在工作、生活多方面给予的帮助照拂,感谢出版社高度负责任的编辑老师。同时,也感谢曾经研究整理出版的张掖各类历史书籍给予我的启发与借鉴,感谢互联网时代各种便利的查阅软件,感谢线上线下自媒体作者与文学爱好者提供相关资料,以及我工作室助理团队帮忙校对。最后,谨以本书献给我早已故去许多年的父母,感谢他们将我带来人世间,生于这片泥土芬芳的传奇厚土。

 甘肃春晚
甘肃春晚 微博
微博 微信
微信